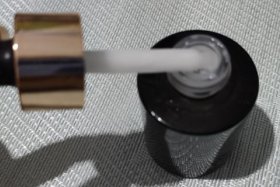司徒雷登,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是陌生又熟悉的名字,也许很多人应该还有印象,他的名字曾经在儿时的课堂上被一遍遍的提到 ,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先入为主的认识。主要是因为他无缘无故的对于中国的热爱,让很多的国人感到陌生和怀疑,所以在司徒雷登最后的岁月 不得不返回美国。当时很多人不解,偌大的燕大校园,竟然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被北大为何反对司徒雷登安葬?司徒雷登当年离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很多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样的信仰,让身为普通人的我们感到陌生。司徒雷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半个世纪前,1962 年9 月19 日,已经半身不遂的司徒雷登,悄无声息地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离开人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隔着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许多年轻人在课堂上不断听到他的名字,他几乎成为那个年代里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人。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无缘无故的爱让国人感到陌生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11 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1887 年他回到美国,1893 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 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1899 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