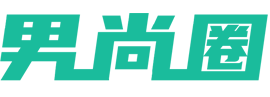陈丹青酒后吐真言内容曝光,老婆黄素宁资料照片首次公开

1995年,陈丹青产生了一个让自己吃惊的念头:所有挂在墙上的画、所有装置作品,都是“静物”。于是他完成了一组15米长、两米高的十联画《静物》,其中的九个画面,是各种
陈丹青作品
陈丹青作品
画册中的当代装置艺术。他想,既然画照片,就可以干脆画书、画画册。两年后,他在地上摊开几本画册,画成一幅写生。此后,他的画册写生一发不可收,他由浓至淡、由繁至简;从西方美术史图像转向中国画图像;从一堆叠放的书到一本摊开的书。他常把不同时期、不同的印刷品放到一起画。
陈丹青说:“如今我与国画的关系已经颠倒错乱:除了守着一摊油画工具,我变得不爱看油画。古人说,称阅读不如背诵,背诵不如抄写。绘画亦然。倘非亲手临摹,此前我莫说不曾‘懂得’,甚至谈不上‘看见’国画——奇怪,经由临写国画,我的油画手艺长进了,我却恍然自以为真的是在画国画。”
直面生活
陈丹青于2000年回国后,曾带着学生去北京二道沟村“下生活”,画农民、退伍军人,去矿区画井下工人,也曾在国外美术馆临摹世界“原典”。他时刻呵斥自己:放老实一点,回到写生,坚持写生。这是一个图像时代,而一直坚持写生、写实的陈丹青称自己是活在一个“前现代”社会。他排斥依赖照片,一如他当年仅靠速写便画出了《西藏组画》。
2010年,陈丹青与杨飞云策划了两个大型美展——《回到写生》《面对原典》,分别在中国美术馆、中国油画院展出。从徐悲鸿、刘海粟等到当下画家,三代人的写生、临摹作品第一次集体亮相。陈丹青在展览序言里直陈:写生、临摹所凸显的中国油画学习与实践中所产生的概念模糊、意义错位以及艺术精神浮于绘画之上等问题。陈丹青指出:写生与临摹有可能被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轻视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生更是逐渐被贬值,大家就对着照片画画,写生已经在画家实践中全面退场,30年来,全国院校师生的写生能力,一代不如一代,而事实上第一代的写生仍没有过关。

画家的作家
作为作家的陈丹青,出版了一系列文学作品:《纽约琐记》《外国音乐在外国》《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十几部书。内容涉猎社会、文化、艺术、教育、文学、人物、历史、音乐、建筑、两性、城市等等方面。其中2005年出版的《退步集》售出10万册,至今已第19次印刷;《多余的素材》在北京三联书店上柜仅一周,便以近千册的销量登上排行榜;陈丹青的书都是畅销书的头几名,香港2008年最受欢迎50本书,第一个就是他的《荒废集》,而且台湾也将出版他的书。写作是他于绘画、演讲之外的又一巨大影响。
陈丹青曾问读者,“为什么喜欢读我的文章呢?”有人答:“大约我们压抑太久了吧。”还有人答:“看你的文字很爽。”陈丹青文字的魅力,部分源自性情、器识;另一部分则和他的画一样,建基于强大的写实功力。他有捕捉并且再现细节的天赋。人性的深浅、文化的歧变,在他眼里不过是有质感的日常细节。
快意的冲突
关于绘画与写作,陈丹青如是说:“很多感受没法放到画里面去,因为绘画就是绘画,它说的是另外一套语
《纽约琐记》
《纽约琐记》
言。但写作可以让我很好地表达:比如纽约我不会去画他,但我可以写它,这是写作过瘾的地方。《纽约琐记》尽可能地描述一个真实的,你可以有呼吸感的空间,我只是以一个纽约居民的身份写这本书的,而不是一个海外艺术家,我不认为有什么动物叫海外艺术家。”
“我得承认,书写、演说,令我获得绘画从未给予的快意,而当闭嘴描画时,我再三庆幸画画比我所能想象的幸福,更幸福。人不免有外向或内敛的天性吧,写写画画,是在均衡这天性,抑或是一种我目前尚未了解的冲突?而绘画与写作的功效,比我想象的更差异。前者是享乐的,自私的,后者似乎迎合公众,并被赋予暧昧的责任。”
“画家的陈丹青”“作家的陈丹青”“演讲家的陈丹青”“评论家的陈丹青”……屡屡而为的跨界,陈丹青锤炼出愈发敏锐多变的眼力和笔力,《退步集》《纽约琐记》《荒废集》表明了陈丹青是个善于思考和善于记录的人,生活的积累在他的身上和文字中酝酿得越发厚重且沉郁。